今天要來聊聊一台車,還有一個跟車一樣固執的人
你知道嗎,有時候你會做一些回頭看覺得「我當初是腦子哪裡有問題」的決定。對我來說,買下那台二手的 S197 野馬就是其中之一。
那是我第一次跟正規經銷商買車,口袋裡的錢其實不太夠,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踏進了什麼樣的坑。說真的,這根本不是一個理性的決定。就是...你知道的,一種衝動。結果就是,隨著時間過去,新的問題一個個冒出來,然後那些我一開始沒注意到的舊瑕疵,慢慢變成了我心裡的疙瘩,整天想著它們。
我的生活變得很快,身份一直在變,但這台車...它就停在那裡,老樣子。
剛開始開它的時候,我真的小心翼翼。對於能控制這台充滿原始力量的危險機器,心裡是又敬又怕。我會靜靜坐在車裡,只是為了感受引擎點火那一瞬間的物理和聽覺上的爆炸感。在州際公路那種有弧度的上坡上,我會一邊拉高轉速一邊像個孩子一樣大笑。真的超爽。
第一年的冬天我還捨不得開,把它好好地停在車庫裡。但夏天一到,我就把所有家當塞進車裡,一路從羅德島殺到肯塔基。在路上,我穿梭在那些大卡車之間,沒有一台車能從我旁邊超過。那是一種很純粹的、人車一體的感覺。
我還記得有一次,在肯塔基一條又長又直的路上,太陽超大,我把油門踩到底。引擎好像很開心地接受了挑戰,彷彿在說「再來!再來!」。我從一台大貨櫃車旁邊呼嘯而過,感覺自己被死死地壓在座椅上,像是要衝破大氣層的太空人。就在我呼出一口氣的瞬間,那個草莓紅色的時速錶指針,親吻了錶底的極限。心臟跳得跟什麼一樣。然後,我鬆開油門,那股腎上腺素才慢慢退去。說真的,那之後,我再也沒那樣開過車了。

車沒變,但我變了
我開著它穿越玉米田、沿著鐵軌、經過無數的穀倉和廢棄建築,回到我蹣跚學步後就再也沒去過的老家小鎮,只為了拿一份出生證明的認證副本。我也開著它在冰雹中殺到亞特蘭大,然後六個月後,我成了爸爸,又開著它回到亞特蘭大,把它運到洛杉磯,再裝船送到韓國。兩年後,它又橫渡太平洋回到美國,陪了我一年多。
這中間,我真的超痛苦,一直在想要不要賣掉它。你知道嗎,那種有倒車顯影、原廠保固、鋰電池的新車,真的很有吸引力。拥有一輛「就只是一輛車」的幸福...一輛不會每天用一張長長的待辦事項清單來煩我的車。一輛不會再讓我想起那些我不想再碰的東西:攻擊性、魯莽、還有那種與世界的疏離感。
現在的我,常常是慢車道上開得最慢的那台車。路上的陌生人也不再想跟我尬車了,因為他們看得出來我沒興趣。只要心跳稍微加速,或是有任何一點點挑釁的行為,我就會覺得是自己嚴重的個人失敗。我學會了策略性地滑行很長的距離來代替煞車,盡量減少不必要的能量和情緒消耗。
老實說,這台車沒變,它還是那台吵鬧、耗油、充滿力量的野獸。但開車的人,已經不是同一個了。
該留還是該賣?天人交戰的比較表
這問題真的困擾我超久。每次想下定決心,腦子裡就開始上演小劇場。所以我乾脆把它列出來,讓自己看清楚一點。這大概就是我腦內的戰爭實況:
| 評估項目 | 方案A:繼續開這台 S197 野馬 | 方案B:換一台無聊但實際的代步車 |
|---|---|---|
| 每天出門的心情 | 每天出門都像在解任務,但聽到 V8 聲浪又覺得...嗯,這很酷。 | 就...一個交通工具。不會興奮也不會失望,像喝白開水一樣。 |
| 錢包的感受 | 一個無底洞。油錢、稅金、還有不知道明天會壞什麼的驚喜包。 | 省油、有保固,預算完全可控,雖然無聊但是非常安心。 |
| 代表的意義 | 代表我的過去、一個追求完美的傻勁,還有那些瘋狂的歲月。是一段故事。 | 代表我的現在和未來?一個務實的、把家庭放第一位的爸爸。 |
| 維修與保養 | 我為了清輪框內側,用砂紙磨到手指破皮...這就是日常。根本是修行。 | 開回原廠,喝杯咖啡,簽個名,搞定。時間就是金錢啊。 |
| 旁人的眼光 | 還是會有人覺得你是不是想飆車。或覺得你是個懷舊的老派傢伙。 | 沒人會多看你一眼,完美融入車陣中。某種程度上的自由? |
| 最終的爽感 | 偶爾在安全的地方拉一下轉速,那種快樂是錢買不到的...吧? | 看著每個月省下的油錢跟保養費,那種踏實感也蠻爽的。 |
路上的那些思考:從大衛福斯特華勒斯到台灣的路況
原文作者提到了一段大衛.福斯特.華勒斯(David Foster Wallace)在畢業典禮演講《這是水》裡的話,這段話真的超經典,我每次塞在路上堵到快抓狂的時候都會想到。
他大概是說,你可以選擇在塞車時,對那些擋路的大型 SUV、悍馬、V12 皮卡感到噁心,想著他們多浪費、多自私。你也可以想著,那些貼著愛國或宗教貼紙的,往往就是最大、最自私的車,然後他們的駕駛方式也最沒品。你可以想著我們的後代會多鄙視我們浪費了所有燃料、搞砸了氣候...等等。
這段話真的很有趣。在美國,作者看到的是悍馬跟大皮卡。這點跟我們在台灣看到的情況很不一樣,但那種「路怒症」的根源完全一樣。在台灣,惹毛你的可能不是悍馬,你知道的,大概是改了吵死人排氣管的 Altis、貼著超黑隔熱紙讓你完全看不透的 Alphard、或是永遠在最後一秒才變換車道的計程車。
華勒斯的意思是,這些都是你可以選擇的「預設模式」,一種很自然但很糟糕的思考方式。但你其實有另一個選擇:去想像那個開 Alphard 的人,可能剛在醫院輪了整天大夜班,累到快不行了,所以開車有點晃;那個計程車司機,可能家裡有急事,或者他如果不搶這個綠燈,今天就賺不到足夠的錢。
這不是說他們開車的方式就對了,而是說,你有能力去選擇如何詮釋這個世界。這真的...超難。尤其是在台灣的交通地獄裡。但這個想法,至少給了一個出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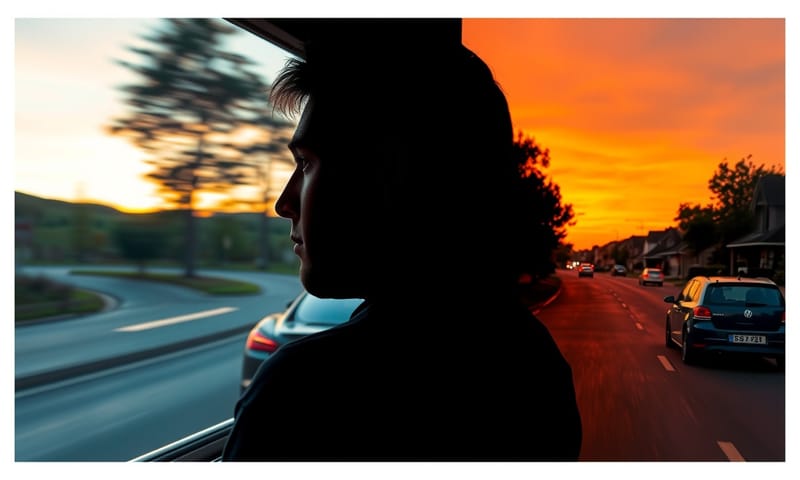
更有趣的是,原文作者也提到,他看到新英格蘭地區滿街的豐田、富豪休旅車,又會想到克林·伊斯威特在《經典老爺車》裡的台詞:「買台美國車會死嗎?」——然後又陷入一種矛盾,一方面希望世界走向潔淨能源,一方面又覺得傳統製造業好像正在消失。
這種感覺我太懂了。這就像我們在台灣,一方面希望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,支持電動車,但另一方面又會擔心,啊,這樣那些傳統修車廠的老師傅怎麼辦?那些玩車的文化是不是會消失?這真的很複雜,沒有簡單的答案。
最後,作者想到了喬治·卡林(George Carlin)的脫口秀:「拯救地球?我們連怎麼照顧自己都還沒學會!」—— 然後他鬆了一口氣,接受了自己的極限。這不是我的錯,這世界本來就很荒謬。
所以,最後的決定是?
當那台改得高高的皮卡從我旁邊呼嘯而過,然後在下一個紅燈前急煞的時候,我只是慢慢地滑行到停止線前。我看了看我車內這堆開始老化的鋼鐵、橡膠、玻璃和塑膠,想起了我花了好幾個小時用砂紙打磨輪框內側,直到指關節都磨破的那個下午。
我想著這台車代表的一切:在一個充滿缺陷的世界裡,追求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完美;在不斷展開的人類故事中,一小片屬於我自己的文化遺產;還有,關於成長,以及努力想成為一個好人的挑戰。
最簡單的做法,就是把它留下來,完成我開始做的事情。再開著它橫跨一次美國,回家,回到我拋在身後的自由。或許,我還會再讓它放肆一兩次。
對,我就把它留著吧。直到它被撞爛——可能是明天,可能是三十年後,也可能永遠不會——直到它只剩下閃爍的記憶和沉入土壤的腐蝕金屬。畢竟,它終究只是一台車。
......
才怪。
我後來改變主意了,把它拿去換了一台雪佛蘭 Bolt 電動車。😂

換你說說看了!
你心裡有沒有一台像這樣,充滿故事、讓你又愛又恨的車(或任何東西)?它代表了你的什麼時期?最後你放下了嗎?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吧!



